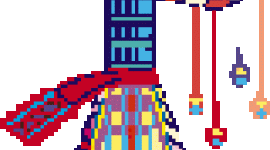阴阳人儿童的医疗管理:童年性虐待的一个类比
简介
医疗程序经常被用作儿童性虐待的类似物,并被视为在自然主义背景下观察儿童对这些经历的记忆的机会(Money, 1987;古德曼,1990;购物者,1995;彼得森·贝尔,出版中)。医疗创伤分享的许多关键元素儿童虐待如恐惧、痛苦、惩罚和失控等,往往会导致类似的心理后遗症(Nir, 1985;他表示,1988;她,1993;购物者,1995)。然而,很难找到一种自然发生的创伤,其中包含了被认为对遗忘/恢复记忆现象至关重要的方面:即保密、错误信息、照顾者的背叛和分离过程。更难找到直接涉及生殖器接触并准确反映发生虐待的家庭动态的医疗事件。
最接近于确定儿童对CSA回忆可能涉及的因素的研究是Goodman等人(1990)的一项研究,涉及经历了排尿膀胱尿道造影(VCUG)测试以确定膀胱功能障碍的儿童。古德曼的研究是独特的,因为它包括了直接的、痛苦的和令人尴尬的生殖器接触,包括孩子的生殖器被穿透和在医务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排尿。古德曼发现,有几个因素导致了对手术的遗忘:尴尬,缺乏与父母讨论手术过程,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这些正是在家庭虐待情况下可能发生的动态。
医疗中间性的处理(这一术语涵盖了广泛的条件,包括不明确的生殖器和性核型)还没有作为CSA的替雷竞技到底好不好用代品进行探索,但可能会为围绕儿童期记忆编码、处理和性创伤检索的问题提供额外的见解。雷竞技是骗人的像CSA的受害者一样,双性儿童雷竞技到底好不好用反复遭受生殖器创伤,这些创伤在家庭和周围的文化中都是保密的(Money, 1986, 1987;凯斯勒,1990)。他们感到害怕、羞愧、被误导、受伤。这些儿童的遭遇就像是一种性虐待(Triea, 1994;大卫,1995 - 6;Batz, 1996;Fraker, 1996;Beck, 1997),并认为他们的父母与伤害他们的医疗专业人员串通一气,背叛了他们(Angier, 1996;Batz, 1996;贝克,1997)。 As in CSA, the psychological sequelae of these treatments include depression (Hurtig, 1983; Sandberg, 1989; Triea, 1994; Walcutt, 1995-6; Reiner, 1996), suicidal attempts (Hurtig, 1983; Beck, 1997), failure to form intimate bonds (Hurtig, 1983; Sandberg, 1989; Holmes, 1994; Reiner, 1996), sexual dysfunction (Money, 1987; Kessler, 1990; Slipjer, 1992; Holmes, 1994), body image disturbance (Hurtig, 1983; Sandberg, 1989) and dissociative patterns (Batz, 1996; Fraker, 1996; Beck, 1997). Although many physicians and researchers recommend counseling for their intersexed patients (Money, 1987, 1989; Kessler, 1990; Slipjer, 1994; Sandberg, 1989, 1995-6), patients rarely rece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are usually reported as being "lost to follow-up." Fausto-Sterling (1995-6) notes that "in truth our medical system is not set up to deliver counseling in any consistent, long-term fashion" (p. 3). As a result, the intersexed child is often entirely alone in dealing with the trauma of extended medical treatment.
如果双性儿童在出生时就被识别出来,他/她将接受广泛的身体、基因和手术测试,以确定最适合抚养的性别。凯斯勒(1990)指出:“医生……暗示孩子的性别不是模棱两可的,而是生殖器…这些例子传达的信息是,问题在于医生判断性别的能力,而不是性别本身。真正的性别可能会通过测试来确定/证明,而“坏”的生殖器(这让每个人都感到困惑)将被“修复”。(16页)。虽然儿童在青春期期间反复接受检查,但往往没有对这些频繁的医疗检查作出解释(Money, 1987年,1989年;Triea, 1994;桑德伯格,1995 - 6;Walcutt, 1995 - 6; Angier, 1996; Beck, 1997). Because both parents and physicians view these treatments as necessary and beneficial to the child, the child's trauma in experiencing these procedures is often ignored. The underlying assumption is that children who do not remember their experiences are not negatively affected. However, medical procedures "may be experienced by a child or adolescent as a trauma, with the medical personnel considered as perpetrators in collusion with the parents... the long-range effects of these events may have serious and adverse effects on future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Shopper, 1995, p. 191).
羞愧和尴尬
古德曼(1994)指出,性在儿童心目中主要表现为尴尬和恐惧。因此,孩子们可能会对所有带有性意味的情况做出尴尬和羞耻的反应。她认为,“孩子们对带有性意味的情况的反应是变得尴尬——他们被教导要有这种感觉,而不一定要理解其中的原因。也许孩子们被教导的关于性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别人暴露自己的身体”(第253-254页)。经历过多次VCUG的孩子更有可能对最近的测试表达恐惧和尴尬,并且在测试发生后哭过。一些人甚至否认他们做过VCUG。
接受其他类型生殖器手术的儿童也会觉得他们的手术是可耻、尴尬和可怕的。生殖器的医学摄影(莫尼,1987年)、性早熟和阴阳人情况下的生殖器检查(莫尼,1987年)、暴露于DES的女孩的阴道镜检查和检查(Shopper, 1995年)、膀胱镜检查和导管插入(Shopper, 1995年)和尿道下裂修复(雷竞技到底好不好用ISNA, 1994年)可能导致与CSA高度相关的症状:分离(Young, 1992年;Freyd, 1996),消极身体形象(Goodwin, 1985;Young, 1992)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学(Goodwin, 1985)。莫尼的一位病人报告说:“我躺在那里,身上只盖着一张床单,大约10个医生会进来,床单会被扯下来,他们会在我周围感觉,讨论我有了多大的进步……我当时非常非常震惊。然后床单会盖在我身上,其他医生会进来,他们会做同样的事情……太可怕了。我惊呆了。我做过这样的噩梦……” (Money, p. 717)
类似的情况也被其他的双性恋者报道过(Holmes, 1994;桑德伯格,1995 - 6;Batz, 1996;贝克,1997)。像CSA一样,反复的医学检查遵循Lenore Terr称为II型创伤的模式:那些长期和重复的事件。第一次这样的事件当然会带来惊喜。但随后发生的恐怖事件让人产生了一种期待感。大量保护心灵和保护自我的尝试开始运转……长期遭受恐怖袭击的孩子们会明白,压力很大的事件还会重演。”(引自Freyd, 1996, p. 15-16)。 Freyd (1996) proposes that "psychological torment caused by emotionally sadistic and invasive treatment or gross emotional neglect may be as destructive as other forms of abuse" (p. 133). Schooler (in press) noted that his subjects experienced their abuse as shameful, and suggests that shame may be a key factor in forgetting sexual abuse. "The possible role of shame in causing disturbing memories to be reduced in accessibility... might well resemble those sometimes proposed to be involved in repression" (p. 284). David, an adult intersexual, states "We are sexually traumatized in dramatically painful and terrifying ways and kept silent about it by the shame and fear of our families and society" (David, 1995-6). Most intersexuals are prevented by shame and stigma from discussing their condition with anyone, even members of their own family (ISNA, 1995). This enforced silence is likely to be a factor in how their memories of these events are understood and encoded.
保密与沉默
一些理论家假设,保密和沉默导致孩子无法对虐待事件进行编码。Freyd(1996)认为,对从未被讨论过的事件的记忆可能与那些被讨论过的事件的记忆有质的不同,Fivush(在出版中)指出,“当没有叙事框架时……这很可能会改变孩子们对经历的理解和组织,并最终改变他们提供详细和连贯叙述的能力”(第54页)。沉默可能不会阻碍初始记忆的形成,但缺乏讨论可能会导致记忆的衰退或未能将信息纳入个体的自我自传式知识(Nelson, 1993,引于Freyd, 1996)。
当孩子遭受创伤时,许多父母试图阻止孩子专注于这件事,希望这能将事件的影响降到最低。有些孩子被积极告知要忘记创伤;其他人则根本没有表达自己经历的空间。这种动态在双性儿童的情况下尤其有效(Malin, 1995-6)。谢丽尔·蔡斯说:“没关系,不要去想它”,这是我和少数人谈论过的建议,其中包括两名女性治疗师。关于她的双性人身份,她的父母跟她唯一的沟通就是告诉她,她的阴蒂变大了,所以必须切除。“现在一切都好了。但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他们说(蔡斯,1997)。琳达·亨特·安东(1995)指出,父母“通过不谈论“它”来应对,希望减轻[孩子]的创伤。情况恰恰相反。 The girl may conclude from the adults' silence that the subject is taboo, too terrible to talk about, and so she refrains from sharing her feelings and concerns" (p. 2). Both Malmquist (1986) and Shopper have put similar views forth (1995), noting that a child may view the adults' silence as an explicit demand for his or her own silence. Slipjer (1994) noted that parents were reluctant to bring their intersexed children to outpatient check-ups because the hospital served as a reminder of the syndrome they were trying to forget (p. 15).
钱(1986)报告情况下,“雌雄同体的孩子比性区别对待正常的孩子,在这样一种方式表示,她是特别的,不同的,或奇特的——例如,通过让孩子在家,禁止她和邻居的孩子玩,把否决关于两性的通信条件,并告诉孩子在家里躺或回避关于长途旅行诊所访问”的原因(p。168)。北美双性人协会(ISNA)是一个为双性人提供同伴支持和倡导的组织,它指出,“这种沉默的阴谋”……事实上加剧了双性青少年或年轻人的困境,他们知道自己是不同的,他们的生殖器经常被“重建”手术残缺,他们的性功能严重受损,他们的治疗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承认或讨论[他或她的]双性行为违反了文化和家庭禁忌”(ISNA, 1995)。
Benedek(1985)指出,即使是治疗师也可能不会询问创伤性事件。创伤受害者可能会认为这是治疗师的一种声明,表明这些问题不是讨论的安全话题,或者治疗师不想听到这些问题。她建议,复述和重播故事是受害者掌握经验并将其纳入其中的一种方式(第11页)。考虑到此类讨论的频率,CSA受害者和双性恋者经常因为他们的经历而经历负面的心理后遗症也就不足为奇了。
错误信息
另一方面,施虐者对现实的重构(“这只是一个游戏”,“你真的想让这发生”,“我这么做是为了帮助你”)可能会导致孩子缺乏对虐待记忆的理解和存储。像CSA受害者一样,双性儿童经常被错误地告知他们的经历(Kessler, 1990;David, 1994,1995 -6;Holmes, 1994,1996;黑麦,1996;斯图尔特,1996)。父母可能会被鼓励不让孩子知道自己的状况,理由是“在青春期之前告诉孩子这种状况会损害孩子的自尊”(Slipjer, 1992, p. 15)。父母经常被错误地告知在他们的孩子身上实施的程序以及对他们的孩子可能产生的结果。一位医学专业人士(Hill, 1977)建议“明确地告诉父母,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不会有不正常的性欲,因为外行会把雌雄同体和同性恋弄得不可思议地混淆”(第813页)。与此相反,ISNA的统计数据显示,“很大一部分间性恋者会发展成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或双性恋成年人,或者选择改变性别——无论是否进行了早期手术修复或重新分配”(ISNA, 1995)。
安吉拉·莫雷诺(Angela Moreno) 12岁时被告知,出于健康原因,她必须切除卵巢,尽管她的父母已经知道了她的真实状况。安吉拉患有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AIS),这种情况下,XY胎儿在子宫内对雄激素没有反应,出生时具有正常的女性外生殖器。在青春期,隐伏的睾丸开始产生睾丸素,导致她的阴蒂增大。“他们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要切除我的阴蒂。我在杜冷丁的烟雾中醒来,感觉到纱布和干涸的血液。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会这样对我而不告诉我。”(Batz, 1996)
马克斯·贝克每年都被送往纽约接受治疗。“当我进入青春期时,有人向我解释,我是一个女人,但我还没有结束……(治疗结束后)我们会回家,一年后再谈这件事,直到我们再次去....我知道这不会发生在我的朋友身上”(Fraker, 1996,第16页)。这种对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件缺乏理解和解释可能会导致他们无法理解他们的经历,并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将其编码。父母和医生强调医疗程序的好处也可能导致情绪失调,阻碍儿童处理经验的能力;当被告知他或她正在得到帮助时,孩子感到受伤。
分离和身体隔阂
为医疗治疗检查阴阳人儿童的记忆可能会对儿童理解涉及他/她身体的创伤性事件的过程有所启发,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记录这些事件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什么。不管父母和医学界的意图如何,由于儿童缺乏将身体边界的跨越理解为破坏性以外的任何东西的能力,儿童时期的生殖器手术可能具有与CSA相同的情感价值。正如莱斯利·杨(1992)指出的那样,性创伤的症状根源于身体是否舒适地生活。
“我的内在”和“我的外在”之间的界限不仅违背了一个人的意愿和最大利益,而是“消失了”……——不是简单的忽略,而是“从未存在过”。在身体上挑战或妥协我的界限,威胁着作为一个生命体的我的毁灭;“在我之外”的东西现在似乎进入了我,占据了我,重塑和重新定义了我,通过将我的内在和外在混为一谈,使我对自己陌生。毫无疑问,在我看来,这次攻击是可憎的,恶毒的,完全是针对个人的,而不考虑任何人类的意图。(91页)
这种困惑在阴阳人儿童中可能尤其严重,他们的身体通过生殖器手术和反复的药物治疗被重塑和重新定义。
在被列为创伤期间分离发作诱因的标准中,Kluft(1984)包括“(a)孩子害怕自己的生命……(c)儿童身体的完整性和/或意识的清晰性被破坏或损害,(d)儿童因这些恐惧而被孤立,(e)儿童被系统地误导或“洗脑”他或她的处境。(引自Goodwin, 1985, p. 160)。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在阴阳人儿童的医疗过程中发挥作用;孩子,被告知几乎没有关于手术和检查的基本原理,对他/她的生活是可怕的,孩子的生殖器手术切除和/或改变,代表一个明确违反物理完整无缺,孩子被孤立的恐惧和质疑他或她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和将来会发生什么),并给出孩子信息,并不能反映真实的自然的治疗或程序的细节。
安吉拉·莫雷诺和马克斯·贝克都报告了广泛的分离性发作。“在我青春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一个会走路的脑袋”Max回忆道(Fraker, 1996, p. 16)。莫雷诺报告说:“经过多年的治疗,她终于觉得自己是在自己的身体里,充实了自己的皮肤,而不仅仅是漂浮着”(Batz, 1996)。这些陈述与CSA受害者的陈述类似,他们报告说,为了承受身体上的侵犯,他们在情感上与自己的身体分离。反复接受阴道镜检查的妇女报告说,她“在阴道检查中幸存下来,完全脱离了自己的下半身——也就是说,腰部以下变得“麻木”,没有感觉或感觉”(Shopper, 1995,第201页)。Freyd(1996)称分离为“对不合理情境的合理反应”(第88页)。Layton(1995)指出,碎片化可能是这些经历的结果:“……如果世界的镜子没有把你的微笑反射给你,而是在看到你时破碎,那么你也会破碎”(第121页)。分离反应在CSA和医疗过程中似乎都是一种防御和后果。
背叛的创伤
Jennifer Freyd(1996)提出,当孩子依赖并必须与施虐者保持密切关系时,更有可能发生这种经历的遗忘。背叛创伤假设有7个因素可以预测健忘症:
1.照料者虐待
2.明确威胁要求保持沉默。环境中的另类现实(滥用背景与非滥用背景不同)
4.虐待期间的隔离
5.年轻时受虐待
6.另一种由照顾者定义现实的陈述
7.缺乏对虐待的讨论。(弗雷德,第140页)
当然,这些因素在阴阳人儿童的医疗管理中起着作用。Shopper(1995年)指出,医疗程序"类似于儿童性虐待的程序,因为在家庭内部往往明显否认儿童的创伤现实。从儿童的角度来看,家庭被视为与实施创伤性手术的施暴者(医务人员)暗中勾结。这种看法可能导致对父母的强烈愤怒反应,也会影响对父母保护和缓冲能力的信任感”(第203页)。相反,为了保持与父母的关系完好无损,孩子可能会抑制对这种背叛的承认。Freyd(1996)指出,“对外部现实的记录可能会受到维护他人爱的需要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当他人是父母或值得信赖的照顾者时”(第26页)。她还指出,孩子对施害者的依赖程度越高,照顾者对孩子的权力越大,创伤就越有可能是一种背叛。“受信任的照顾者的背叛是决定创伤失忆的核心因素”(第63页)。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孩子与父母的关系都可能被破坏。这可能发生在创伤发生时,如果孩子认为父母没有保护他或她免受痛苦的经历,或者后来当孩子恢复或重新解释这些早期的经历时。Freyd(1996)认为,有些人在意识到背叛时,会通过对事件形成新的理解,或者通过对背叛事件进行恢复(第5页),意识到事件的全部影响。对事件进行内部评估和标记的方式可能是这种恢复体验的关键组成部分(第47页)。Joy Diane Schaffer(1995-6)建议,阴阳人儿童的父母应该得到充分的知情同意,包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阴阳人儿童从生殖器手术中受益....”父母也应该经常被告知,许多在童年接受过生殖器手术的阴阳人认为自己受到了手术的伤害,因此经常与父母疏远”(第2页)。
未来研究方向
在医疗机构内接受阴阳人治疗的儿童与遭受性虐待的儿童经历了许多雷竞技到底好不好用相同类型的创伤。由于几个原因,对阴阳人儿童的治疗经历和他们对这些事件的记忆的研究可能比迄今为止所做的研究更接近童年性虐待的经历。阴阳人疾病的医疗管理包括由对儿童有权力的人直接接触儿童的生殖器,并在其雷竞技到底好不好用父母的合作下。手术过程是痛苦的、令人困惑的、重复的。儿童处境的家庭动态也与家庭虐待中的情况相似:儿童经常被沉默或被错误地告知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父母要为所造成的伤害负责。最后,这些经历的结果导致了非常相似的负面心理后遗症,包括抑郁、身体形象破坏、分离模式、性功能障碍、亲密问题、自杀企图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研究双性儿童的医疗经验的研究设计将为记忆研究者提供明显的优势,而不是那些迄今为止所做的研究。对过去研究的一个根本批评是,难以建立关于CAS事件的“客观真相”。因为虐待通常是隐藏的,除非儿童引起当局的注意,否则不存在任何文件来显示发生了什么。对回顾性研究持批评态度的人指出,因此几乎不可能将成年人的描述与实际的童年事件进行比较(这一规则的主要例外是Williams, 1994a,b所做的研究)。在双性人治疗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可以在诊所或医院获得有关程序和儿童反应的大量医疗文件。双性儿童可以在手术时接受采访,并进行纵向跟踪,以观察他们长大成人后对这些事件的记忆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将允许一个更以过程为导向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创伤经历的童年记忆问题(在缺乏外部支持或存在错误信息的情况下,儿童如何理解和编码创伤?情绪对记忆处理有什么影响?父母互动的作用是什么?)以及成人回忆(创伤的意义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对孩子的社交和情感发展的长期影响是什么? What happens to the family dynamic when adults research their medical conditions and discover that they have been misinformed?). An observation of these children's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strategies for dealing with their medical treatment may shed some light on how these processes operate for victims of child sexual abuse.
编者按:塔玛拉·亚历山大在精神上与ISNA成员马克斯·贝克结婚已近四年。这对夫妇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安家。当她不写论文和为孩子做计划的时候,塔玛拉就忙着抚养他们的四只猫,一只狗,以及埃默里大学心理学本科生的意识。欢迎异性伴侣与她联系,相互支持。
©1977版权所有Tamara Alexander
参考文献:阴阳人儿童的医疗管理
娜塔莉·安吉尔(1996年2月4日),《两性间疗愈:一个异类找到一个群体》。《纽约时报》。
琳达·亨特(1995)。说话的禁忌。别名:AIS支持小组通讯,1,1,6 -7。
巴茨,珍妮特(1996,11月27日)。第五性。《河滨时报》,[在线]947。可用:
http://www.rftstl.com/features/fifth_sex.html/
朱迪·贝克(Max)(1997, 4月20日)。个人通信。
Elissa P. Benedek(1985)。儿童与精神创伤:当代思想的简要回顾。在S. Eth和R. S. Pynoos(编),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第1-16页)。华盛顿特区:美国精神病学出版社。
追逐,谢丽尔。(1997)。感到羞辱的原因。在D. Atkins (Ed.), Looking Queer。纽约州宾汉姆顿:霍沃斯出版社。
大卫(1994)。我不是一个人!来自大卫的个人日记态度的雌雄同体[北美阴阳人协会季刊],1(1),5-6。
David (1995-6, Winter)。临床医生:向双性成年人寻求指导。态度的雌雄同体[北美阴阳人协会季刊],7。
Fausto-Sterling,安妮。冬天(1995 - 6)。是时候重新审视旧的治疗模式了。态度的雌雄同体[北美阴阳人协会季刊],3。
Fivush, Robyn, Pipe, Margaret-Ellen, Murachver, Tamar和Reese, Elaine(印刷中)。说出和未说出的事件:语言和记忆发展对恢复记忆辩论的影响。M. Conway(编),恢复的记忆和错误的记忆(34-62页)。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弗雷克,黛比(1996,9月19日)。雌雄同体站出来抗争:新的“双性人”运动挑战着对矫正手术的需求。南方之声,14-16页。
Jennifer J. Freyd(1996)。背叛创伤:遗忘童年虐待的逻辑。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古德曼,g.s.,库斯,j.a.,巴特曼,方斯,j.f.,里德尔斯伯格,m.m.,库恩,J.(1994)。预测童年经历的创伤事件的准确记忆和不准确记忆。在K. Pezdek和W. Banks(编),恢复记忆/错误记忆的争论(第3-28页)。纽约:学术出版社。
古德曼,盖尔S.,鲁迪,莱斯利,波顿斯,贝蒂L.和阿曼,克里斯汀(1990)。儿童的关注和记忆:儿童目击者证词研究中的生态有效性问题。在R. Fivush J.A. Hudson(编),幼童的认知和记忆(第249-294页)。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
古德温,琼。(1985)。乱伦受害者的创伤后症状在S. Eth和R. S. Pynoos(编),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第155-168页)。华盛顿特区:美国精神病学出版社。
山,沙龙。(1977)。生殖器不明确的孩子。美国护理杂志,810- 814。
Morgan Holmes (1995-6, Winter)。我还是个双性人。态度的雌雄同体[北美阴阳人协会季刊],5-6页。
Morgan Holmes(1996)。对瑞切尔的采访。来自加拿大的态度[加拿大阴阳人协会通讯],1,1,2。
赫蒂格,安妮塔·L.,拉达德里希南,贾扬特,雷耶斯,埃尔南·M.和罗森塔尔,Ira M.(1983)。男性化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症治疗后的心理评价。中华儿科外科杂志,18(6),887-893。
北美阴阳人协会。(1994)。尿道下裂:家长指南。[可从北美阴阳人协会获得,邮政信箱31791,旧金山,CA 94131]。
北美阴阳人协会。(1995)。治疗建议:阴阳人婴幼儿。[可从北美阴阳人协会获得,邮政信箱31791,旧金山,CA 94131]。
苏珊娜·凯斯勒(1990)。性别的医学建设:双性婴儿的病例管理。标志:文化与社会中的女性杂志,16,3 -26。
库兹,伊恩,加尔布,罗纳德和大卫,丹尼尔(1988)。心肌梗死后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医院精神病学杂志,10,169-176。
琳恩·莱顿(1995)。创伤、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碎片化的话语。美国影像杂志,52(1),107-125。
马林,H.马蒂(1995-6,冬季)。治疗引发了严重的伦理问题。态度的雌雄同体[北美阴阳人协会季刊],8-9。
Malmquist, C.P.(1986)。目睹父母被杀的孩子:创伤后方面。美国儿童精神病学学会杂志,25,320 -325。
Money, John, and Lamacz, Margaret(1987)。生殖器检查和暴露经历在医院性虐待在童年。神经与精神疾病杂志,175,713 -721。
约翰,德沃尔,霍华德,和诺曼,伯纳德F.(1986)。性别认同和性别换位:32名男性两性人被分配为女孩的纵向结果研究。性婚姻治疗杂志,12(3),165-181。
Nir, Yehuda(1985)。患癌症儿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在S. Eth R. S. Pynoos(编),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第121-132页)。华盛顿特区:美国精神病学出版社。
彼得森,C.贝尔,M.(印刷中)。儿童创伤性记忆损伤。孩子的发展。
赖纳,威廉·G.,吉尔哈特,约翰,杰夫斯,罗伯特(1996,10月)。膀胱外翻的青少年男性心理性功能障碍。儿科:1996年美国儿科学会年会上发表的科学报告摘要,88,3。
莱,B.J.(1996)。在AIS家族中。加拿大的态度[加拿大阴阳人协会通讯],1,(1),3-4。
大卫·桑德伯格(1995-6,冬季)。需要进行研究。态度的雌雄同体[北美阴阳人协会季刊],8-9。
桑德伯格,大卫E.,梅尔-巴尔伯格,海诺F.,阿兰诺夫,盖亚S.,斯康佐,约翰M.,亨塞尔,特里W.(1989)。有尿道下裂的男孩:行为困难的调查。儿童心理学报,14(4),491-514。
Schaffer, Joy Diane (1995-6, Winter)。让我们在等待研究结果的同时获得知情同意。态度的雌雄同体[北美阴阳人协会季刊],2。
斯库勒,j.w.,本迪克森,M,和安巴达尔,Z.(出版中)。从中间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同时容纳对性虐待的虚构记忆和恢复记忆吗?在M. Conway(编),虚假和恢复的记忆(页251-292)。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Shalev, Arieh Y., Schreiber, Saul, and Galai, Tamar(1993)。医疗事件后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英国临床心理学杂志,32,247-253。
购物者,Moisy(1995)。作为创伤来源的医疗程序Meninger诊所通报,59(2),191-204。
Slijper, f.m., van der Kamp, h.j., Brandenburg, H., de Muinck kezer - schrama, S.M.P.F, Drop, s.l.s., and Molenaar, J.C.(1992)。先天性肾上腺增生年轻女性性心理发育的评估:一项初步研究。性教育与治疗杂志,18(3),200-207。
Slijper, f.m.e., Drop, s.l.s., Molenaar, j.c.和Scholtmeijer, R.J.(1994)。生殖器官发育异常新生儿指定女性:家长咨询。性教育与治疗杂志,20(1),9-17。
斯图尔特,芭芭拉(1996)。负担减轻了。加拿大的态度[加拿大阴阳人协会通讯],1(1),3。
特里亚,基拉(1994,冬季)。的觉醒。态度的雌雄同体[北美阴阳人协会季刊],1,6。
Walcutt, Heidi (1995-6, Winter)。被文化神话折磨的身体:布法罗儿童医院幸存者的故事。态度的雌雄同体[北美阴阳人协会季刊],10-11。
威廉姆斯,琳达·梅耶(1994a)。童年创伤的回忆:女性童年性虐待记忆的前瞻性研究。临床与咨询心理学杂志,62,1167-1176。
威廉姆斯,琳达·梅耶(1994b)。在有儿童性受害记录的妇女中恢复了受虐待的记忆。创伤性压力杂志,8,649 -673。
莱斯利·杨(1992)。性虐待和肉体化问题。儿童虐待与忽视,16,89-100。
©1977版权所有Tamara Alexander
APA的参考
Staff, H.(2007年8月9日),《阴阳人儿童的医疗管理:儿童性虐待的类比》,HealthyPlace。2021年4月9日,从//www.lharmeroult.com/gender/inside-intersexuality/the-medical-management-of-intersexed-children-an-analogue-for-childhood-sexual-abuse获取